苏欣
2008年2月10日,山东淄博。农历新年的余温尚未散尽,立春时节的微寒中,一场不期而至的春雪飘然而落。就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上,诗人章伟写下了这首仅有十二行的短诗《雪》。这枚晶莹的语言晶体,如一片真实的雪花般轻盈,却在它极简的构造中,承载了关于时间、记忆与存在的全部重量。本文试图穿越那些看似平易的词语,探寻这首诗如何在“一片”与“好多年”的张力中,构建起一座属于现代汉诗的微形神殿。
一、雪的语法:从物象到灵晕的嬗变
诗歌始于对“雪”的命名,却立即偏离了命名的确定性。“一片/一瓣”,这组并置的量词构成了诗歌的第一个玄机。在汉语的日常使用中,“片”属于平面几何的范畴,指向剪纸般的薄度与规整;而“瓣”则源自植物或嘴唇的生理构造,暗示着有机体的弧度与柔软。两种度量体系的并置,使雪在进入语言的瞬间就分裂为二重存在:既是非生命的降水,又是有生命形态的摹本。
这种分裂在第三行完成了决定性的跳跃。“或是你嘴角/轻轻的/微笑”。“或是”这个连词在此并非提供选择,而是执行了一次危险的等同:雪或许是微笑,微笑或许是雪。当物(雪)与人(嘴角)通过“微笑”这一短暂的面部表情达成互换,一种新的知觉伦理便诞生了——自然现象不再是人的隐喻背景,而直接成为情感本身的可触形态。微笑的“轻轻”与雪花的飘落共享着同一重力法则:不是坠落,而是悬浮;不是终结,而是过程。
德国哲学家本雅明曾用“灵晕”(Aura)描述艺术品那种“在一定距离之外但感觉上如此贴近之物的独一无二的显现”。在章伟的雪中,我们目睹了自然物获得灵晕的瞬间:雪不再仅仅是H₂O的固态结晶,而成为可以凝视、可以怀念、可以与之对话的“你”。这种物我互渗的知觉方式,接通了中国古典诗学“物色带情”的传统,却又在现代汉语的简洁中获得了新的尖锐性。
二、时间的拓扑:风在前而身影在后
如果第一节是空间的诗学,那么第二节“好多年/风都是这样吹着口哨/走在前面/后面铺满你的身影”则展开了时间的悖论。风“吹着口哨”的拟人化处理,赋予时间以孩童般的无辜面孔——它并非残酷的收割者,而是一个吹着不成调曲子的漫游者。然而这轻松表象下,“走在前面”四个字暴露了时间的暴力本质:它永远领先于我们,我们永远在追赶却永远落后。
真正颠覆认知的诗行在最后:“后面铺满你的身影”。在物理世界中,身影永远投射于行进者的前方(当光源在后)或脚下(当光源在上)。而“后面铺满身影”创造了一个不可能的拓扑结构:身影如地毯般在身后铺展,仿佛行走不是创造新的地面,而是不断展开一卷早已绘就的画卷。这是记忆的形而上学——过去并非被抛在身后逐渐模糊,而是在身后不断累积、加厚,成为我们背负的可见风景。
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在《差异与重复》中提出,真正的过去并非线性消逝,而是以“纯粹过去”的形式整体共存于每一当下。章伟以诗的方式抵达了相似的洞见:那些“好多年”并非一去不返,它们以“身影”的物质性沉淀下来,成为此刻行走的基底。“铺满”这一动作的完成时态至关重要:这不是正在发生的过程,而是已经完成的状态。记忆不是收藏,而是地层。
三、日期的重量:2008年2月10日的雪
诗末标注的创作日期“2008年2月10日于山东淄博”绝非无关信息。这一年年初,中国南方正经历一场罕见的雨雪冰冻灾害,这场自然灾害与同年8月北京奥运会的喜庆形成微妙的历史对位。而淄博——这座齐国故都、现代工业城市——在传统与现代的撕扯中,恰好是当代中国的一个缩影。
然而诗歌对这一切集体记忆保持了绝对的沉默。这种沉默不是逃避,而是以诗的纯粹性进行的另一种见证。当历史试图用宏大叙事覆盖个体经验时,诗歌退回到“一片/一瓣”的微观知觉;当时代喧嚣要求人们向前看,诗人却执意凝视“后面铺满”的身影。这种逆向的注视,构成了对单一进步史观的温柔抵抗。
农历新年刚过的时节赋予了这场雪以仪式性意义。在中国文化语境中,春节是家庭时间与历史时间的交汇点,人们在这一刻同时面向祖先(过去)与后代(未来)。章伟的雪恰好落在这一时间褶皱里:它既是新年伊始的征兆,又是对“好多年”的蓦然回望。雪的飘落完成了时间的收束——所有的时间层同时在场,如身影般铺满身后的大地。
四、沉默的技艺:现代汉诗的减法美学
《雪》的惊人之处在于其极致的简洁。全诗实际只有九个意象单位:雪、一片、一瓣、嘴角、微笑、好多年、风、口哨、身影。诗人进行了一场严格的语言减法,剥除了所有修饰、阐释、议论,直至只剩下意象的骨骼。这种减法美学呼应了现代主义诗歌的“排除原则”,却又不同于西方现代主义的碎片化倾向——中国的留白美学在此转化为结构性的沉默。
诗中动词的稀缺同样值得注意。除了“是”(隐含在“或是”中)、“吹着”、“走在”、“铺满”,几乎没有其他动作。尤其是“铺满”这个动词,以被动形态(身影被铺满)表达了最大的主动性:不是谁在铺,而是铺这一状态自身在发生。这种语法上的暧昧,使记忆成为自动写作的主体。
在韵律上,诗歌放弃了外在的押韵规则,却在内部创造了气息的节奏。“一瓣”与“微笑”通过“嘴角”的连接形成意蕴上的押韵;“口哨”与“身影”则通过“前面/后面”的空间对位达成呼应。这是呼吸的韵律而非音乐的韵律,它要求读者以同样轻柔的气息参与诗的完成。
五、雪的谱系:在与古典的对话中
将章伟的《雪》置于汉语诗歌的雪意象谱系中观察,会显现其独特的现代位置。古典诗歌中的雪,无论是柳宗元“孤舟蓑笠翁,独钓寒江雪”的孤绝,还是白居易“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”的温情,抑或《红楼梦》“白茫茫大地真干净”的虚空,雪始终是背景、是环境、是心境的外化。
而在章伟这里,雪成为了主体。它不是被观看的风景,而是观看本身;不是情感的喻体,而是情感的本体。这种转变的完成,关键在于“或是”二字创造的知觉革命——当雪“或是”微笑,物与我之间那道自笛卡尔以来坚固的主客壁垒,在汉语的柔性智慧中悄然消融。
与当代诗歌中其他著名的雪相比,如北岛《雪》的社会批判锋芒,或海子《雪》的神性追寻,章伟的雪更接近现象学意义上的“回到事物本身”。它不象征超越,也不指向批判,它只是如其所是地呈现:雪作为雪,同时作为微笑,作为记忆的显影剂。
六、作为记忆术的诗歌
在《雪》的末尾,时间呈现为奇异的折叠形态:“好多年”被压缩进“一片”雪的瞬间,而瞬间的雪又延展为“铺满”身影的无限平面。这种时间体验,恰如普鲁斯特在《追忆似水年华》中描绘的:一小块玛德琳蛋糕的味道,足以唤醒整个贡布雷的童年世界。
章伟以十二行诗构建的记忆装置提醒我们:真正的记忆不是档案馆中的分类收藏,而是如雪般飘落的偶然相遇。那些看似消逝的时光,其实都如身影般铺展在我们身后,等待一场雪般的词语将它们照亮。诗歌在此成为最精密的记忆术——不是记录发生了什么,而是保存“发生”本身的结构。
2008年春天的这场雪早已融化,但“一片/一瓣”的追问仍在继续。当风依旧吹着口哨走在前面,我们这些行走者终于理解:诗歌的意义不在于预言未来,而在于教会我们如何转身,看见身后那片由所有逝去时光铺成的、柔软而坚实的大地。在那里,每一个微笑都如初雪般崭新,每一片雪花都承载着整个冬天的重量。
这或许就是为什么,我们需要在每一个下雪的日子,重新阅读这样一首小诗。它告诉我们:记忆不是负担,而是大地;时间不是流逝,而是沉淀;而诗歌,就是那片让我们在漂浮中获得重量的、永不融化的雪。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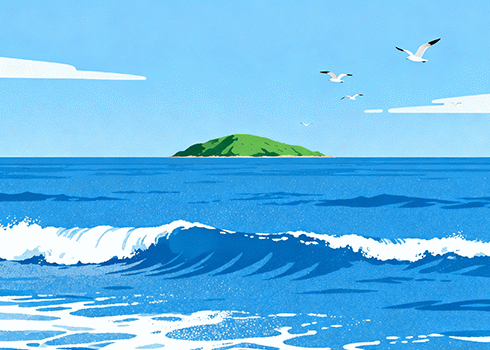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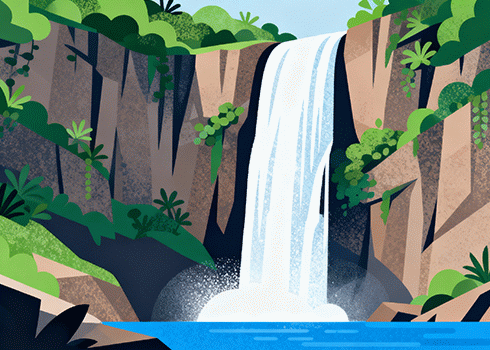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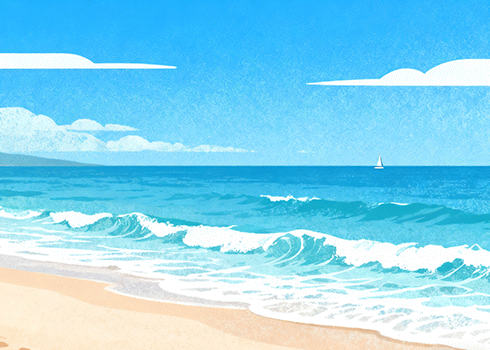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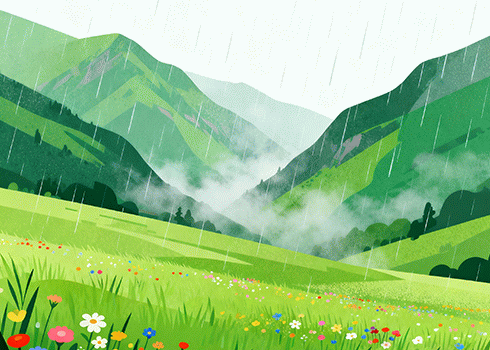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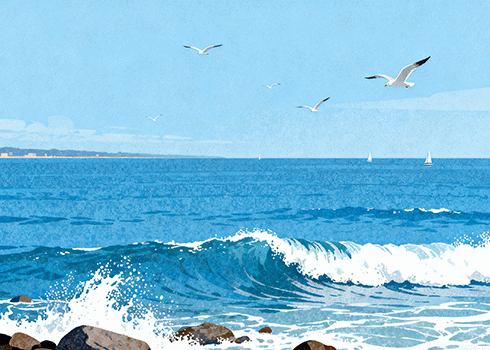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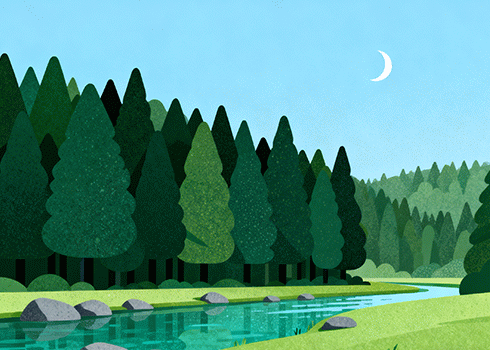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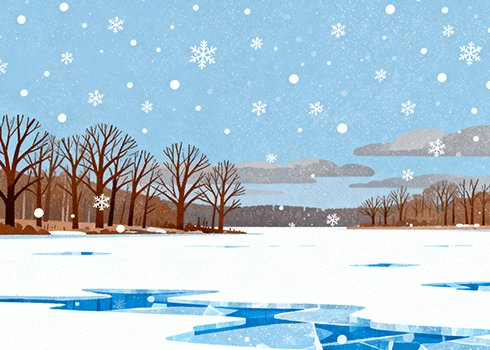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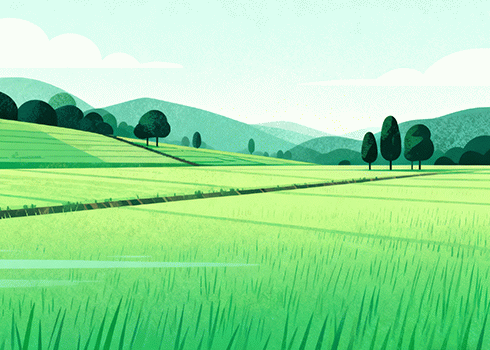
《冰雪中的生命低语与永恒追寻——读章伟的《雪》》等您坐沙发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