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成亮
章伟,这位在当代诗坛中静默耕耘的写作者,如同他的许多诗作一般,并未被广泛的目光所凝视。他的诗往往在寻常物象的褶皱里,藏匿着关于存在、疾病与死亡的幽微思考。2009年5月25日于长春写就的《白血病蟑螂》,便是一首在极简语言下涌动着复杂生命辩证的短章。在这首诗中,“白血病”与“蟑螂”——两个在文化象征谱系中近乎相反的意象被强行并置,前者指向纯洁的受难、血液的病变与生命的脆弱,后者则关联着肮脏、顽强与令人厌恶的生存。这一看似悖谬的标题,已然揭示了诗歌的核心张力:生命如何在最卑微、最受诅咒的形式中,同时展现其不堪一击与坚韧不拔的双重面相。
诗歌开篇并未直接呈现标题意象,而是构筑了一个悬置而恍惚的日常场景:“白兰瓜在果篮里凝视 / 谁的目光在凝视里行走”。白兰瓜,一种洁净、甜腻、近乎无菌的水果,在“果篮”这个被规整的容器中,竟然产生了“凝视”。这拟人化的“凝视”是空洞的,还是满载意义的?它旋即被一个更游移的主体——“谁的目光”所穿行。主客体关系在此模糊,凝视者反被凝视,稳定的感知秩序开始松动。紧接着,“电影里的声音已经忘记 / 脚下的鞋子悄悄躲起”,听觉与视觉的连续性被切断,连最贴身的物件“鞋子”也具备了自主意志“躲起”。这四行诗构建了一个失序的、物我关系颠倒的微观世界,仿佛一种疾病(无论是生理的“白血病”,还是存在的“不适感”)悄然侵入,瓦解了日常经验的可靠性。它为“蟑螂”的出现铺设了一个知觉上已然溃败的舞台。
第二节,目光转向关系性与社会性的溃败。“谁跟在谁后面 / 谁走在谁前面”,这不仅是空间次序的迷失,更是人际连结与身份参照的丧失。当人无法在关系网络中确认自身位置时,一种根本的孤独与失向便油然而生。随后,“黑色的胡须从来没有扬起 / 看到的人都四散着离去”,这里的“黑色胡须”或可视为蟑螂触须的隐喻,但它“从来没有扬起”,失去了探测与交流的功能。而“看到的人”的反应是“四散着离去”,这是对异类、对病态、对令人不安之物的本能排斥与恐惧。蟑螂,作为闯入人类洁净空间的“他者”,它的存在本身便是一种冒犯,引发驱逐的集体无意识。这何尝不是对疾病患者(尤其是如白血病般具有某种“不可见”却致命的内患)社会处境的精准隐喻?病患常常在成为被观察的客体时,也成为了被疏离、被隔绝的客体。
正是在这种双重的溃败(知觉的与社会的)之后,抒情主体发出了一声交织着叹息与诘问的呼喊:“脆弱的你呵 / 脆弱的人呵”。两个“脆弱”的叠用,将“蟑螂”(“你”)与“人”(“我”或泛指的人类)置于同一情感平面上。这种等同是惊人的,它打破了物种的尊卑层级,在“脆弱”这一根本的生命境况前达成共情。蟑螂因其卑微与肮脏而被蔑视,却拥有顽强的生命力;人类自诩为万物灵长,却在疾病、孤独与存在的虚无面前不堪一击。标题中“白血病”对“蟑螂”的修饰,此刻获得了更深的理解:这或许并非一只患病的蟑螂,而是蟑螂这一意象本身,被赋予了如白血病般矛盾的特质——它既是生命力顽强的象征(如蟑螂的生存能力),又内嵌着一种本质性的、源于血液的脆弱与纯净的病变(如白血病)。
最终,诗歌结束于一个感知的困境:“我如果能看得清 / 为何你总是离开我的眼睛”。“看清”是理解的象征,是试图把握对象、赋予其意义的努力。然而,“你”(蟑螂/脆弱生命/疾病的象征)却“总是离开我的眼睛”。这种“离开”既是物理上的隐匿(如蟑螂躲入缝隙),更是认知上的逃逸。我们无法真正“看清”疾病,无法真正“看清”死亡,也无法真正“看清”那种如蟑螂般既令人厌恶又令人惊叹的原始生命力。它总在我们定义的边缘,在我们目光试图聚焦的刹那,滑入阴影之中。这最后的诘问,充满了哲学性的无奈,它承认了理性与感知在面对生命终极悖论时的限度。
《白血病蟑螂》全诗仅十二行,语言极简,意象奇崛,在有限的篇幅内完成了一次对生命复杂性的深刻勘探。章伟通过将“白血病”与“蟑螂”这两个充满对抗性的符号并置,迫使我们重新审视关于纯洁与肮脏、脆弱与顽强、疾病与生命、人类与他者的一系列既定分类。诗歌中的“蟑螂”,不再是单纯的害虫象征,而成为一个承载着生存悖论的复合体:它背负着“白血病”所隐喻的、内在于生命的缺陷与苦难,却同时以其顽强的“蟑螂”式存在,嘲笑着人类对洁净、秩序与不朽的幻想。在章伟克制的诗行下,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对生命本身深深的敬畏与悲悯——生命正是在其最不堪、最受诅咒的形式中,彰显着它那无法被彻底规训、无法被完全“看清”的、黑暗而磅礴的力量。这力量,既令人恐惧,也令人动容。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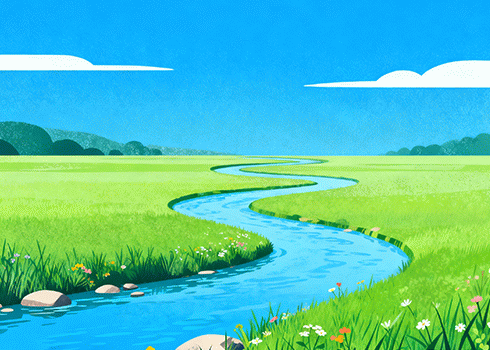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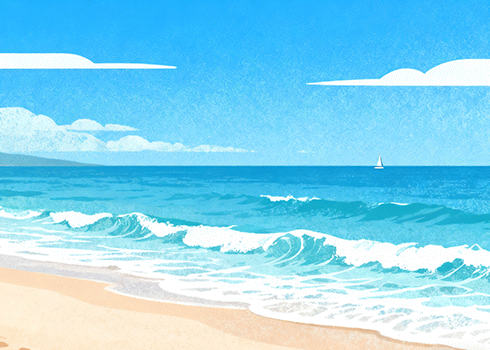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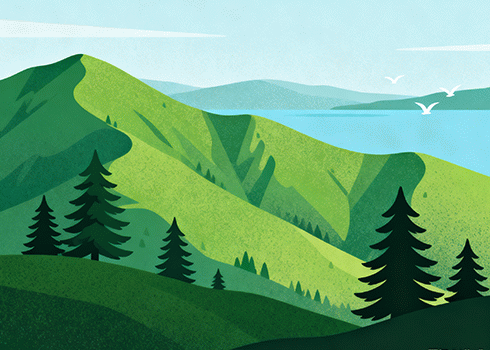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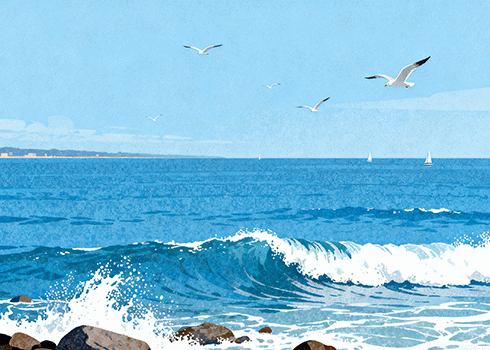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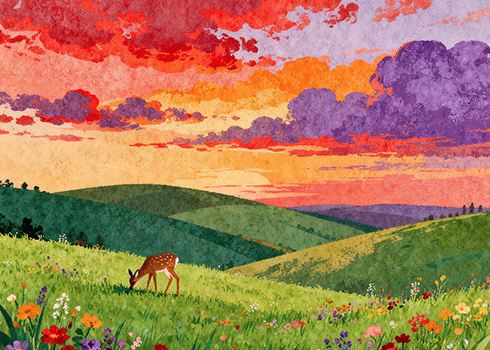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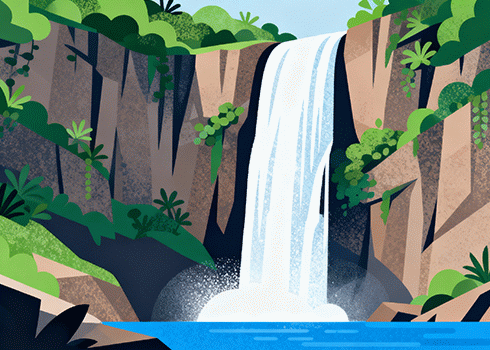
《脆弱的顽强:章伟《白血病蟑螂》中的疾病隐喻与生命辩证》等您坐沙发呢!